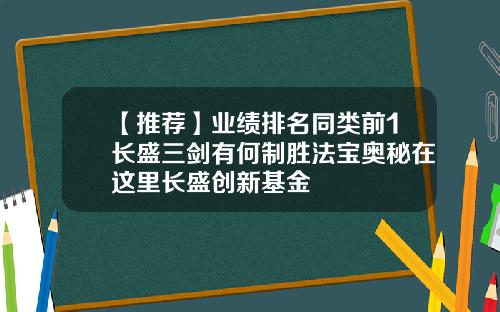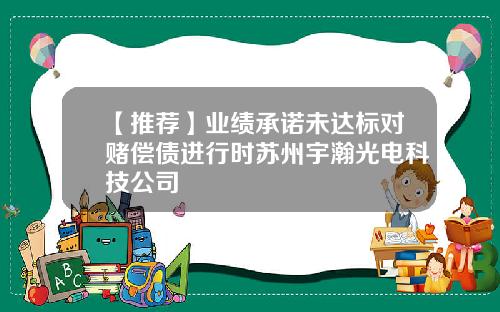「博学苑」从墓葬壁画看辽金大同地区饮食文化
王利霞/文
摘要:自公元10至13世纪,在我国北方出现了强大的辽金王朝,它一出现便与中原的宋王朝形成对立局势,当然这种对立局势是暂时的。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中,辽金政权与中原的宋王朝文化交流频繁、经济往来密切。在此基础上,辽金境内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那么,作为辽金五京之一的西京地区在饮食文化上与其他地区又有那些共性与不同呢?本文以大同地区出土的辽金壁画墓为研究素材,从中颉取宴饮、备食、侍酒、侍茶等表现备食、饮食场景的壁画内容,以此来解读辽金时期大同地区出土的壁画所蕴含的饮食文化。关键词:大同;墓葬;辽代;金代;壁画;饮食
辽金王朝是兴起于我国东北部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07年,以耶律阿保机为首的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起了割据政权,与后来的北宋、西夏形成三足鼎立的局势。辽朝疆域广阔、物产丰富,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存在了两百余年,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民族文化。契丹立国后,政治上实行“南北面官制”,经济上农牧结合,文化上加强与北宋与中西亚之间的交流,由此造就了辽国丰富多样的人文生活。公元1125年,女真族灭辽,建立大金国。金国依然在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上,承继辽与中原的文化因素,形成了独特的生活习俗,二者表现在饮食方面则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饮食文化。西京大同作为辽金五京之一,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区域特征,辽金历代皇帝都非常重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得西京地区的农业、手工业、畜牧业呈多样化发展态势,而这些又与饮食有着密切联系。近年来,大同地区发掘的数十座辽金壁画墓中,出现了不少备宴、饮食等场景。本文以这些考古资料为研究对象,并加以详细整理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索辽金时期大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概况。
图1:大同周家店辽墓备膳图
一、大同地区的辽金壁画墓
大同地区辽金墓葬分布相对较多,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该地区发掘、清理的辽金墓葬约有五十余座,其中壁画墓二十座,分别为辽代十七座,金代三座,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大同北郊、西南郊及南郊地区。为方便研究,笔者将大同地区辽金壁画墓的相关信息作了简单整理(见表1),并以此对壁画中所体现出来的饮食文化信息加以提炼分析与对比研究。
表1:大同地区辽金壁画墓
从目前大同地区出土的壁画墓来看,辽代壁画墓占绝大部分,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辽金墓葬共有五十余座,其中辽代墓葬就有四十余座,金代墓葬近十座,占比近80%,除却该地区形成的特有葬俗习惯外,大同在辽代历史地位要重于金代也是很重要的事实。大同地处辽地西南边陲,是辽国南下中原、西入夏国的边关要塞与重要枢纽。“澶渊之盟”以后,大同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得以迅速发展。重熙十三年(1044年),辽兴宗升云州为西京,大同是为辽五京之一,此后成为辽国西南边地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政治地位的提升,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加强了西京地区民族融合进程,更是促进了该地区各行各业的发展,加快了社会经济繁荣。反应在墓葬方面,则是出现了大批陪葬器物丰富、壁画装饰精美的墓葬,如新添堡许从赟夫妇墓、卧虎湾辽墓群、西环路辽墓群、东风里辽墓等等。这种墓葬壁画装饰从辽早期至晚期都有发现,壁画内容以人物、宴饮、备膳为主,其次为少量的出行以及生活起居图。就大同辽代壁画墓而言,早期以人物图为主,兼有少许出行准备的场景,中晚期则多以人物图、备宴图、出行图为主,并以此形成固定的区域装饰内容。通常墓室北壁绘人物图或侍寝图(但值得一提的是,与辽腹地的墓室北壁一般会出现墓主人形象不同的是,大同地区的辽中晚期墓葬中在墓室正壁隐去了墓主人的形象,只出现侍者人物形象),墓室西壁绘出行图或出行准备图(也有在西壁靠近车马出行图的地方绘宴饮的场景,如卧虎湾辽墓群),东壁绘宴饮或备膳场景,南壁(即墓门两侧或甬道两侧)则以侍者或门神形象出现。到了金代,壁画装饰内容又发生了明显的区别,辽代西壁的出行图像不在显现,代之以盛大的宴饮散乐场景,而东壁则同样以备膳、侍宴为主,北壁与南壁延续辽代绘画内容,多以侍者人物形象出现。由此来看,不论是辽代或金代,宴饮或备膳图在墓葬壁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图2:大同南郊云大M1宴饮图(局部)
二、壁画墓中的饮食场景
辽金时期,大同地区的饮食种类丰富、制作方法多样,这些在墓葬壁画中同样有体现。根据近年来大同地区出土的辽金壁画墓中有关饮食场景的内容来分析,具体包括备膳、宴饮等方面。
(一)备膳壁画
大同新添堡M29备膳图2副,一副绘于墓室西壁与出行图毗邻,画面前有长桌,桌上放置多件碗、碟以及盘等食用器具,桌旁站立着三位女侍者,均头梳高髻,着浅黄色上衣,其中两人作斟酒态势,另一妇人则手捧食盒。另一幅绘于墓室东壁,画面中绘长方形桌,在桌上置数件碗、碟,另有一带碗注子。桌子旁边站立三位男性侍从,皆头戴幞头,身着长袍。
大同西环路M1备膳图,壁画位于墓室西壁,画面中一侍女头梳高髻、面部红润、宽额方脸,上身着粉红色宽袖衫,颈露青灰色中单,下身着青色长裙,右手托大型圆托盘,左手扶盘边缘。侍女前方有一方桌,其上由南向北依次放置一件白色细颈带盖执壶、一件红色椭圆形盘、三间盏托及一件红色瓜棱形包裹,以此表示备菜与备饮的场景。
大同南关M2备膳图,壁画位于墓室东壁,画面中绘三人,站成一排,皆着窄袖圆领长袍。右边一人为男性,束发,身着紫色长袍,左衽,腰系青绿色带,脚蹬尖头靴,双手捧盘,盘中盛放着桃子、梨等水果。中间一人同样为男性,束发,身着黄色长衫,双手叉手于胸前。左边一人为女性,梳双髻,着青绿色长衫,腰系带,脚穿尖头靴,双手托一盘与胸前。少女面带微笑,似与身旁两人作交谈状。三人身前地面上放置方形火盆,火盆四周饰壶门,门内有火,火盆上放置一短流长把注壶。
大同周家店辽墓备膳图2副,其中一幅位于墓室东北角,画面下方绘一长方形火盆,盆内火势较旺,盆后绘一方形炕桌,桌上放置多子盒、箱、碗等饮食器具。桌左侧绘两侍女,一前一后,前边侍女席地而坐,头梳高髻,身着交领宽袖长袍,目视火盆。后边侍女站立,头梳高髻,着交领宽袖掩脚长裙,双手捧以黑色托盘,内置一碗。画面右侧绘有两位侍女和一位男侍,其中右侧一侍女头梳高髻身着交领宽袖掩脚长裙,双手捧一桃形食品,侧身面向火盆方向。左侧男侍身着圆领窄袖长袍,左手托一盘食品,侧身面向右边侍女,似作交谈状( 见图1)。另一幅位于墓室西北角,画面上方为土红色砖雕直棂窗,窗下绘一长方形桌,桌上放置了多子盒、盘、碗以及各种食品等。方桌两侧各绘一身着官服的侍者,侧身相对,作交谈之态。
大同和平社M45备膳图,壁画位于墓室东壁,脱落严重,残存壁画仅可看到画面中绘一四腿方桌,桌上制碗筷。桌后面绘有两位侍从,一人只留有底部长袍,另一人上身残缺,可看到着宽袖长袍,双手隐于袖内作拱同样胸前。
图3:大同南郊云大M2宴饮图(局部)
大同南郊云大M1备膳图,壁画位于墓室东壁,画面右侧绘六位侍女,左侧绘2位男侍。侍女均头梳高髻,身着掩脚襦裙,右起第一位双手捧以托盘、盘中置一小盅;第二人右手执壶,正专注地往盅里注酒。第三人双手隐于袖中,仅露右手拇指,身体略右倾,神情安详,似在倾听身边侍女谈话。第四人左臂举于胸前,拇指与小指翘起右手提裙裾,侧面面向第三位侍女,似作交谈状。第五人为女童,第六人双手捧一黑色托盘,上置一盏,侧脸面向身后女童。左侧两男子二人侧身相对,皆戴幞头,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脚蹬尖头靴。其中一人左手举于胸前,另一人双手捧一唾盂,身体右倾,与左侧男子作交谈状。
(二)宴饮壁画
大同卧虎湾M1的宴饮图,壁画分为两组均绘于墓室西壁,靠近车马出行图,其中一组绘两位侍者,身着浅蓝色、橙黄色的外衣,中间绘一方桌,桌上放置注子、盏托等饮具;另一组绘两位着红黄服饰的人物坐于桌旁,桌子上置注子、荷叶形盏等饮具。桌旁站立一人,身着黑花蓝衣服,手执琵琶,作弹奏状。
大同卧虎湾M2的宴饮图,与M1类似,一幅绘于墓室西壁,画面中置一长形桌,桌上有注子及和野性小蝶等饮食器具。桌旁站立两人,皆头戴展角幞头,身着长袍,作对饮姿态。另一幅绘于墓室东壁,为乐官一组十二人,皆身着长袍,腰系带,手执笙、箫、笛、琵琶、拍板、大鼓、腰鼓、方响等。
大同卧虎湾M4的宴饮图,同样有两副,一幅绘于墓室东壁,一组七人,有的头戴东坡巾,有的戴展角黑色幞头,有的梳髻,均手捧盘、碗、盒、碟等饮食器具,与画面中牵棕红色马的人站在桌旁边,作相互谦让的宴饮之状。桌上置各种食物,方桌左下方绘一炉灶及烧饭侍者。方桌左侧绘以侍女,头梳双髻,身着秘色圆领长袍,站在微启的大门边,面朝右边宴饮的人们,作侧身观望之态。另一幅绘于西壁,同样一组七人,均手捧各类食具,和牵着黄牛的人站在桌旁边,作宴饮之状。桌上放置各类食物及饮食器具,画面内容与东壁基本相似,唯一不同的是,在画面右侧绘一门,门内外各绘一侍童,一人在门内,头顶饮盘,另一人在门外,提水壶。人物前方绘一方桌,桌上罩有黄色帷幔,上放置碗盆等食用器具。
大同东风里辽墓侍酒散乐图,壁画位于墓室东壁,画面中绘有五位中年男性侍从,均头戴黑色幞头,留小髭胡,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脚蹬黑色长筒靴,朝墓室北壁恭立。前排左起第一人双手端一黄色托盘,盆内只两盏;第二人左手托一注壶,右手握壶柄。后排左起第一人双手执以黄色拍板;第二人双手捧以托盘,盘内放置石榴、黄桃等水果;第三人右手握成拳状于胸前,左手执物。在人物前面又绘有黄色盝顶、圆顶食盒、盛有食物的圆盘黄色酒瓶以及放置于炭火盆的三把小执壶等。
大同南郊云大M1宴饮图,壁画位于墓室西壁,画面中绘六男一女,男子皆戴幞头,身着圆领窄袖长袍,腰系带。右起第一人双手捧一盘,盘中置盅;第二人双手握笙正作吹奏状;第三人双手握着拍板正在表演,第四人双手握笛;第五人左右手举于胸前,各执一乐器;第六人双手捧浅盘,盘中置一盅。人物前面绘一方桌,桌面罩有黄色帷幔,上放置碗、钵、纱罩(内放置食物)、注壶等器具。(见图2)
大同南郊云大M2宴饮图,壁画位于墓室西壁,画面中绘八位男侍,均戴幞头,着圆领窄袖掩脚长袍。左起第一人手捧唾盂;第二人手端一盘,内盛六个桃形食物;第三人双手举于胸前;第四人手捧一盖有纱罩的器皿,内置食物,侧身与第三人作交谈状;第五、第六两人侧脸相对,作交谈之貌;第七人手捧一案,内放置桃形食品;第八人手捧一盘,盘内置一小碗。人物左前方绘一长方形桌,桌面罩帷幔,上放置案、碗、盏、注子、纱罩(内有食物)等器具。(见图3)
大同站东徐龟墓散乐侍酒图,壁画位于墓室西壁,整体画面为一个大房间,房内两侧有挽起的蓝色帐幔,画面偏左有一长方形高桌,上置曲沿盆、高足小方盘(盘内盛似为苹果、桃、葡萄之类的水果)、勺、盏、注壶、梅瓶等。高桌左侧绘一侍女,双手捧一浅蓝色橄榄形瓶,侧身向桌上的曲沿盆被倒酒(或水)。高桌右侧放一筝台,台面上放置一七弦琴,筝后坐一抚琴女。高桌及抚琴女后面站立一排共七位侍女,均头梳高髻,上身着窄袖交领襦服,下身着长裙。左起第一人左手拿一展开的簿册,右手执笔作记录状;第二人双手举于胸前并执一柄小团扇;第三人右手在上,左手在下,执觱篥作吹奏状;第四人双手执笛作吹奏之态;第五人双手拿一拍板作击节状;第六人双手捧一套注壶;第七人双手捧一方盘,盘中放一荷叶形盏。(见图4)
图4:大同站东徐龟墓散乐侍酒图
三、壁画中反映的饮食文化
与辽代腹地的墓葬壁画相比,大同地区的壁画主要以备膳(备饮)和宴饮场景以及人物侍奉图为主,鲜少有狩猎图、出行归来图以及烹饪图。首先,这与大同地区以农耕为首、农牧结合的经济形态有关。尽管西京大同地处塞北,为辽金政权重要的边陲之地,但其地理上与中原腹地较近,历史上受中原文化影响颇深,而其经济结构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其次为手工业、畜牧业。因此,该地区的墓葬壁画中并不见畜牧或狩猎的场景。其次,就大同地区的辽金壁画墓而言,不论是壁画人物的着装服饰、仪容仪表,还是壁画中茶酒、饮宴、劳作生活的场景,亦或是壁画的整体布局以及墓中的各类随葬器物,都能够明显看出唐宋文化的痕迹。由此来看,辽金时期的草原游牧文化对西京地区的影响甚微,而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应是该地区的主流文化。当然,这种文化形态是结合了北方游牧文化的因子,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地域性,这在壁画中的饮食场景都有体现。
辽代立国以后,大力发展农业,尤其占据燕云十六州以后,农业经济发展日盛,农产品种类繁多,与此相对应的面食品种更加丰富。《辽史·礼志二》记载:“大臣敬酒,皇帝饮酒。契丹通,汉人赞,……赞各就坐,行酒肴、茶膳、馒头毕。从人出水饭毕,臣僚皆起”。《事物纪原》又载:“古之馒头有馅,用猪、羊肉之以面,像人头”。由此可见,辽金时期的“馒头”应与如今的肉包相似,而在壁画中也常见这类食物。如大同市南郊云大M1中的宴饮图,在画面中央的长方形高桌上放置一纱罩,而纱罩下又放着数个白色圆形食物,笔者猜测应是馒头或包子一类的面食品。再如南郊云大M2中的宴饮图,左起第二位男侍者手端一盘,盘内盛放着六个白色桃形食物,第四人双手捧着一盖有纱罩的器皿(与M1中的纱罩类似),纱罩内又放置六个白色带褶圆形食物。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位侍从手中端着的是馒头或包子之类的面食。在人物前方的高桌上又放着一个较大的纱罩,内有数个大小不等、涂着黄色或红色的圆形食物。那么这些带有颜色的食物是否是面食品呢?依据大同辽金壁画以及同时期其它地区的壁画内容来看,纱罩内通常放置热食,因此这些食物是面食品应是无疑的。至于涂着颜色,这在其它壁画及相关史料中并未见到,笔者猜测可能是画工师傅故意为之。除此外,还有饼、饼饵、艾糕之类的面食品,不过这些在壁画中鲜少出现,但出土的随葬器物可以证实这类食物的存在,尤其面饼应是西京地区重要的面食品种。该地区的辽代许从赟夫妇墓及云大金墓群都出去了铁质鏊盘。《正字通》中记载:“鏊,今烙饼平锅约饼鏊,亦约烙锅鏊”,《玉篇·金部》中又写道:“鏊,饼鏊也”,由此可见,鏊盘应为古时烙饼的一种工具,其做法是先将鏊置于炉火之上,再将擀好的面饼放置于鏊面上,待饼烙好铲出,面饼形状类似于现在新疆地区常食用的馕。由此可见,这类器物在大同地区的辽金墓葬中都有出现,充分反映出面饼是该地区重要的食物之一。
除面食外,蔬菜同样是辽金时期人们的重要食物,不过这时期蔬菜的食用方法相对简单,通常为生食或做羹汤,亦或是将蔬菜与米混合做成带菜的米饭,如《辽史·张俭传》记载,辽兴宗临幸张俭家后,“进葵羹干饭,帝食之美”。获取燕云之地以后,农副产品种类增多,蔬菜的品种也相对丰富起来。西京地区就栽培韭菜等各类蔬菜,同样这里的人们也喜欢采摘新鲜的野菜吃,《全辽诗话》中有载,辽政事舍人刘经在奉使宋朝的路途,“路中有野韭可食,味绝佳”,于是作诗:“野韭长犹嫩,沙泉浅更清”。不过,在大同地区的辽金墓葬中并没有出现相关菜肴的场景,但在有的备食图中绘着食盒等器具,如大同周家店辽墓东北角的备膳图和西北角的待客图,在画面中都绘有一张长方形高桌,桌上放置着多子盒(即多件盒,通常在一个大的圆盒中放着数个小盒),这些盒中放着的极有可能是菜肴一类的食物。
此外,大同地区还盛产苹果、李子、梨、杏等新鲜水果,在壁画中也出现了这类食物。大同市站东金代徐龟墓西壁的散乐侍酒图中,在画面的长方形高桌上,放置着一个高足小方盘,盘内盛有苹果、桃、葡萄之类的水果,而在桃把上还有数片绿叶,以此说明了水果之新鲜可口。在高足小方盘的右侧上方又有一绛色高足大方盘,盘内盛放着西瓜、石榴等水果。由此来看,辽金时期西京大同的果副品种十分丰富。
酒在古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每逢祭祀、婚嫁、丧仪、欢娱、生儿育女、重要吉日以及文人聚会等等都要以酒行事,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出现了众多的饮酒现象,由此饮酒之风极为盛行,到了辽金时期饮酒更盛。辽代出现了专门管理酿酒的机构,如上京大内西南置有麹院、东京置麹院使,以此对酒实行专卖,征收酒税。到圣宗、兴宗时期,酿酒业更为发展。燕云地区自古有酿酒传统,该地区农作物种类较多,故有“蔬菜果实、稻粱之类糜不毕出”,丰富的农作物品种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西京大同“矾麹尤盈”,“麹”,凡指酒,说明该地区酿酒业十分繁荣,而在该地区辽金墓葬壁画中的备膳图、宴饮图、备饮图出现的饮酒场面以及器型不一、式样丰富的酒具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如大同东风里辽墓的侍酒散乐图,画面中的两位侍者一人双手端着一黄色托盘,盘内放置两个小盏,另一人则双手捧一带碗注壶,表现倒酒备饮的场景。在人物前方放置一长条形矮脚桌,桌上置两个大小不一的酒瓶(矮桌上应带有圆孔,在孔内放置梅瓶或鸡腿瓶一类的酒具,起到稳固作用),在矮桌左前方有一曲沿多足火盆,盆内有炭火,火堆中放置了三把小执壶,以此来起到温酒之用。在大同南郊云大金墓群的壁画中也有类似的场景,如M1的备膳图,右起第一位侍女双手捧托盘、盘中置一小盅,而与其相邻的第二位侍女则右手执壶,正神情专注地往盅里注酒,画面极为形象生动;而在M1的宴饮图中同样有这样的画面,壁画中右起第一位和第六位侍者均双手捧一浅盘,盘中置一小盅,在人物前面的高桌右前方放置了一套黄色注壶和数件敞口盏。上述提及到的梅瓶、鸡腿瓶、注壶以及盏、盅等皆为辽金时期典型的酒具。由此说明,该地区饮酒之风盛行。除酒外,饮茶也是辽人重要的风尚,如墓葬壁画中出现的茶盏及执壶等,皆为表现饮茶之风的场景。
总之,由大同地区辽金墓葬中的壁画来看,不论是从饮食方式、进食过程,亦或是饮食种类、食用器具等,该地区的饮食文化深受中原汉族饮食风俗的影响,以农产品为主,畜牧产品相对较少,而与之对应的肉食品在壁画中表现的更少,这与辽金腹地的饮食文化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诸如上述一再提及的大同地区的饮食文化承袭中原饮食习俗,具有鲜明的中原化特征。
参考文献:
[1]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机车厂辽代壁画墓[J],文物:2006年第10期.
[2]山西大同市辽代军节度使许从赟夫妇壁画墓[J],考古:2005年第8期.
[3]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J],考古:1960年第12期.
[4]同上
[5]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J],考古:1963年第8期.
[6]同上
[7]同上
[8]同上
[9]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西环路辽金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5年第12期.
[10]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J],考古:1960年第12期.
[11]同上
[12]同上
[13]王银田.山西大同市辽墓的发掘[J],考古:2007年第8期.
[14]同上
[15]同上
[16]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和平社辽金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世界:2018年第5期.
[17]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年第10期.
[18]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J],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19]同上
[20]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J],考古:2004年第9期.
[21]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J],考古:1960年第12期.
[2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西环路辽金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5年第12期.
[23]王银田.山西大同市辽墓的发掘[J],考古:2007年第8期.
[24]同上
[25]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和平社辽金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世界:2018年第5期.
[26]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J],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7]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J],考古:1960年第12期.
[28]同上
[29]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J],考古:1963年第8期.
[30]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东风里辽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年第10期.
[31]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J],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32]同上
[33]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市金代徐龟墓[J],考古:2004年第9期.
[34] [元]脱脱.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4月.
[35]高承.事物纪原·卷九·馒头条,“丛书集成初编本”
[36][明]张自烈.正字通[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7月.
[37]胡吉宣.玉篇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1月.
[38][元]脱脱.辽史·张俭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