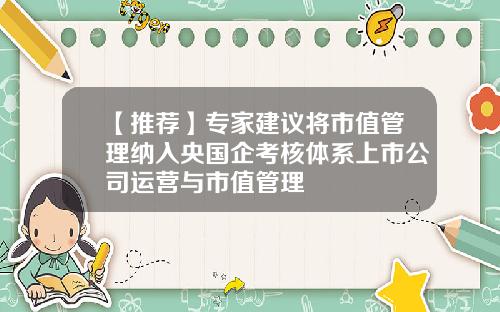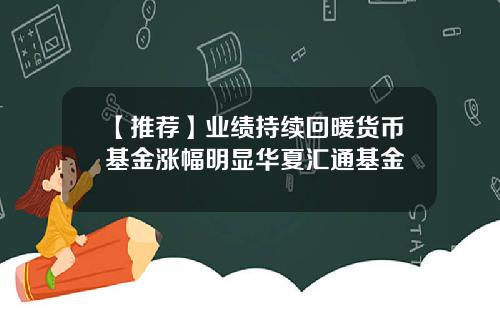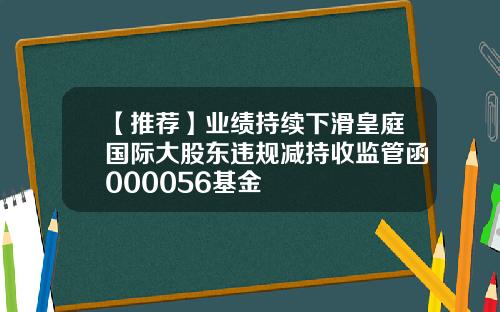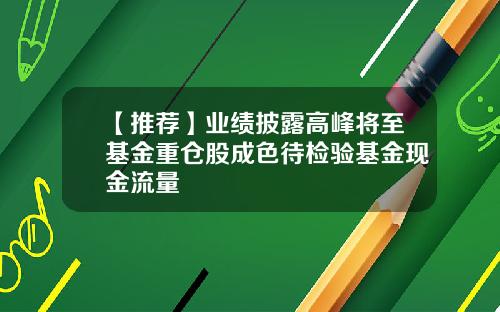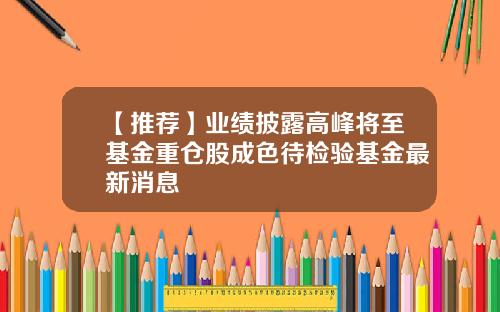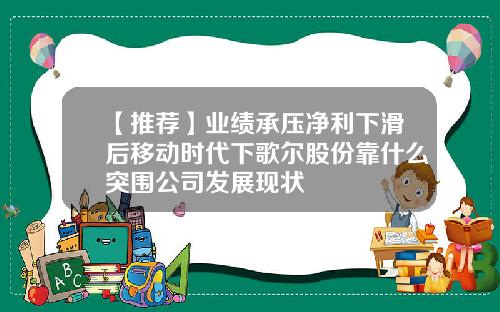刘韡:一个观念艺术家的现实主义
▲艺术家:刘韡
导言2月6日,刘韡的个展“颜色”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开幕。策展人田霏宇这样概括这个展览的看点:“在当代中国如此复杂又充满视觉冲击力的一个语境下,能结晶出什么样的美学观念是我们关心的。我认为答案会比较接近我们将会在’颜色’展览展厅里能看的。”——作为70后最受到关注与认可的观念艺术家,刘韡即保持着新锐度,又己具有某种了代表性,也因此承担着一份高度的期待。
展览开幕前三天,我们走进了如同“刘韡”的布展现场:“施工”基本完成,工人们有些在打扫地面,有些则在刘韡的指示下进行着细节的微调。十来天的布展,每天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深夜,艺术家营造着一个等待被人们领略、惊叹、猜测、赞赏,或是困惑的现场,这本身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就像参观一部电影拍摄中的片场,如果说这些作品之于艺术家来说,是演员、剧本与表演的结合,那么作为导演的艺术家,又如何在反复的“排演”中来完成一次关于“真实”的言说呢?还有比一个观念更惊心动魄与无关痛痒的事情吗?
▲刘韡:《看!书》 展览现场 2014 书、木头、钢 尺寸可变 摄影:唐萱 图片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不断地想自己怎么去让它更有理由在这个地方。”
布入展厅,首先给人第一印象是“大”,所有的作品都是大体量。一组由旧帆布构成的矩形长方体“布阵”成一个迷宫,这组作品的名字本身也叫《迷宫》,从材料上延续了2012年在长征空间个展上集中展示的帆布系列。这组作品依旧象征着丛林与现实,“丛林”的意象很大程度来自于刘韡的个人经验,而现实则可以从那些巨大帆布身上烙印着的国营生产单位字样上,直观地唤起人们关于集体经济生产时代的记忆。人们可以在《迷宫》中穿行,感受,回忆,甚至坐下来,呆一会儿。在帆布矩阵中,还有一组由木头、书本及铝片制作的几何形体,或许对应着现实历史中的人们的形而上迷思。
进一步进入展厅之后的另外两件作品,则营造了充分的距离感,护栏制造了人们无法轻松跨越的高度,把作品与观众隔离开来,让人感觉到一种隔离感的不适,而这正是刘韡希望实现的效果。除此之外,刘韡认为围栏也意味着“狩猎”,在对观念的围堵中,思想与意识与观看者及思考者之间构成了“追逐”与“围捕”的关系。
被围起的作品之一叫《迷局》,镜面制作的形体组成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古代园林的结构,不规则与不对称性,错落有致,这些都是古代园林的美学,但其间的局部又夹杂着刘韡切割物体的某些线条,使之具有了陌生感。在刘韡看来,镜面的光则象征着“光阴”与“命运”。
另一件被围起来的作品叫《看!书》坐落在靠墙一侧,与这组迷幻的“镜花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组由书本堆积切割成的几何形体,零星散落着,相互依靠,却不发生任何交集,搭配着一座貌似苏联风格的小型建筑,整体来看,萧条而又落漠。
位于《看!书》与《迷局》之后的是《受难》,四面高立的墙对立,铝皮制作的不同“框架”,或相反,或重叠,它们表达了关于“演进与迭代”的进程,正如消失的风格。
与11年在民生美术馆的三部曲所营造的线性顺序不同,此次展览的布局,刘韡认为是星座般散落的。在刚刚介绍的几件大作品之间穿插着一些架上绘画,刘韡的“紫气”系列。与此同时,最为炫目的效果来自于一块巨大的荧光屏构成的作品《转变》,布展当天,我们无缘得见其效果。据说这块屏幕会播放的影像作品放射出多种颜色,作品《迷中迷》的镜面会被这些颜色反射到全场。这也是对应展览名字“颜色”的点晴之笔。——“我是一个视觉艺术家,我的表达是视觉,颜色是我们看待事物的一种方式,它覆盖于概念与材料之上,构成了我们区分事物、态度、阶级、好恶、以及一切的万物。” 刘韡说,但同时“颜色的转变是没有原因的,只是为了转变而转变,这件设备和屏幕本身,它的体量及其形式的简单且不断变换的方式,是我对于商业的某些方面的想像。”
早在几年前,刘韡的一次展览名为“万物”,现在看来,这次又是一次“宏观”的展示,它创造了一个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系统:古典、现代、东方、西方、命运、光阴、艺术、商业……诸多概念都有可能被涵盖其间,它们的意义重点不在于自身,而在彼此的对应,建构这个时空的关键这处在于搭建“关系”,在“关系”的交互中才能产生意义。
关于展览,刘韡说:“在我做展览的时候,可能并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是知道我不要什么,把不要的东西全部丢掉,剩下的可能就是我想要的,基本上是以这种排除法来建构整个展览。每天推翻一些东西,到最后很大一部分是依据整个展览如何给别人更好的感官传递。其实整个展览的结构还是有各个层面的,将命运的、现实的、启示的、理性的东西放在一起。其实整个展览像是一件作品,最终每件作品消失了,变成一个展览的概念。”
“永远不是解决一个问题,而是不断地去想、去推进,永远无止,没有一个尽头。做它的理由是因为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就像有一个断裂一样,作品需要一个跳跃,也是因为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你才会去做,如果知道什么我就不用做了。对我来说,调整是调整概念,形体是早就已经存在了,大概有这样的情况,就要不断地来挖掘这个概念,不断地想自己怎么去让它更有理由在这个地方。”
▲刘韡:《迷局》 展览现场 玻璃、铝合金 2014 尺寸可变 摄影:唐萱 图片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从“后感性”到“观念”
刘韡1972年出生于北京,父母都是外科大夫,初二的时候,家人为他找到了一位画家做老师。1988年刘韡报考入美院附中,1992年,考入浙美油画系。大学时代,刘韡说自己主要干的事,就是玩儿。“每天就是踢球,各种运动,一帮人也不知道做了些什么,整天晃来晃去,喝酒、聊天……”
“当时浙美的整体氛围非常的自由,老师几乎不约束学生,学生也不会崇拜老师,因为我们学校有全国最好的艺术图书馆,里面全是国外的图书和杂志,介绍的是最当代的思想,最先锋的艺术”,当时的刘韡并不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艺术家。毕业后,刘韡回到了自己的出生地北京,在北京青年报担任美术编辑。与那时也在北京的邱志杰,同事王卫及艺术家石青是很好的朋友。大家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聊的最多的是艺术、展览,彼此在做作品上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这跟刘韡在大学时候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能再重复前人的创作,这成为他们之后做’后感性’展览的初衷。
1999年,第一场有关“后感性”的展览在芍药居举办,这场展览的宗旨在邱志杰的描述中是这样的:“首先必须是刺激的。但不光是刺激一下,然后必须是异样的。但不光是异样而已,它还最终是富于想象力的后感性”。那次展览上的参展作品便是在这样的价值标准下产生的。
在那场展览上,刘韡展出了一件录像装置作品:《难以抑制》,这是刘韡第一件公开展示的作品。作品的内容是:在陈旧破乱的工业化管道间,嵌入了若干小型的显示器,显示器上反复播放着在地上爬行、扭打的裸露躯体。由于录像采用俯拍的视角,人类躯体的自由运动如同昆虫般蠕蠕而动,彷佛超现实主义的梦魇,自由也变成了盲动。从这件作品开始,刘韡有了自由的意志和尝试,也开启了他之后的创作。
从1997年开始工作到2004年辞职,刘韡的状态一直是边工作,边做作品,当时国内做影像、装置作品的人还很少,做这样的作品,不仅花费高,也很难出售,刘韡说:“我们的许多作品都是现场做的,做完之后就扔掉了,每件作品花费几千到上万,有时要花几个月的工资才能做一件作品。再加之2000年左右,当代艺术展经常被查封,一个展览只展出几天就被封的情况是很经常的事”。
2004年,刘韡工资已经六、七千一个月,而且再工作三个月,即将拥有一笔二十多万的买房资金时,他却毫不犹豫地辞职了。人过而立,工作已经稳定的刘韡,从此全身心地做起了一位职业艺术家。刘韡的好运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辞职之前,刘韡一共就卖过两件作品:一件装置,一件摄影,当时那件摄影作品卖了600美元。但刘韡真的就是那么自信,之后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这种自信。
2005年成了刘韡的人生以及艺术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的首次个展在四合苑艺术空间开幕,并首次参加了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韡的作品变得好卖,乌里-希克成了他最早的藏家,同时国外也有许多藏家开始收藏他的作品。除此之外,对刘韡来说,与之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整个思想上的转变:“这个时候开始,我不再做具体的方案,不会再根据一个点子来创作作品,我意识到,我需要更加的独立,用更适合的方式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十年来,刘韡的作品给人的感觉似乎越来越抽象。早期,他画了一幅钻石的绘画,画这幅作品时,故意要将钻石画烂,因为人们知道钻石的本质是什么,只要一想到钻石,美感已经产生了,画的再烂也是漂亮的,吸引人的,就如同某些事物或观念是无法消解的一样,无论看起来多么烂,但还绝对是美丽的。
这种反叛与质疑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刘韡之后的创作中,也因此让他的作品变得有意义可循:比如2006年在北京公社与U空间(现为博而励画廊)举办的“刘韡专有”个展,展出了一组具有暴力感的作品:《反物质》系列,把诸如电视机之类的电器内外倒置,里面的电子原件改成物体的外衣,透露着艺术家对所谓现代生活的嘲讽与不信任感;另外一件作品:《切》表现的是被生生的按照某个角度切去一部分的日常用品。
他一直在延续的绘画作品《紫气》系列:大量运用充斥着混浊感的紫色暗示着环境污染问题,但紫色又往往与“尊贵”或“华丽”等词有着似是而非的关联,比如我们常说的“紫气东来”便暗含着这一层意思。最终画面呈现出的效果并非一片颓然,类似电路板的线条所勾画出的城市轮廓形象消解掉你通常观测到的城市印象,整体色调是神秘与忧郁的色彩并存,同时暗含着现代城市中的光影迷离。
权利、环境、当代城市生活、空间、建筑构成了刘韡的近些年来创作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比如从2007年开始创作的《爱它、咬它》,是用牛皮狗咬胶制作的装置作品,远看稍显贫民窟似的破烂,细看则发现每个建筑物其实都是带有着各式权利色彩的——众多著名国会形象,美术馆按缩小比例制作的模型,这是刘韡对权利机制的怀疑和讽刺。
▲刘韡:《迷中迷》 展览现场 2014 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 摄影:唐萱 图片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不完整的时候才是完整状态”
2012年,刘韡在长征空间的个展,明确地表明对作品及展览“拒绝描述”,这成了展览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孤立的作品没有任何“支撑”,没有名字、没有材质、没有尺寸……甚至前台处的一张简介上明确写着“刘韡拒绝描述这个展览和作品”,这时,刘韡已经放弃了为作品附加某种观念或者意义,或者说,他想要剥离掉物(作品)本身的意义。
刘韡并不喜欢谈论意义,有人会认为这是作为一位观念艺术的宣传策略,而跟刘韡交谈之后,我们相信,意义的不可说,在于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人们往往将之视为作品的唯一价值。在刘韡看来,“精神性与物质性的同时迸发”,当意义找到最恰当的形式的那一刻,才是最美的。而在被解读,被确认之后,作品却成为思想的垃圾。正如他在做《切》这件作品时说:“只有一个物体在不完整的时候才是完整状态,完整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
“当你表达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你所要表达的东西,当你呈现的时候,每个作品基本上是你思想的垃圾,但是这个作品必须存在,只有在这个上面才能继续思考,这是每件作品存在的意义,它提醒你如何知道一个事情。”
“我们不能在一个框架里做事情,有的时候你画着画着突然发现为什么用画笔解决这个问题呢?也许用一句话,用别的简单的东西就可以了,方式很多,画只是我们前面留下来的一个传统而已,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它抛弃掉,需要用更自由的方式去表达,或者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个事物,这个事物本身已经存在了,但是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而且要不断地反思,不断地重新观看已经存在的东西。比如城市的感觉不但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我们在看建筑的时候会通过建筑知道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很多起初的想法是虚假的,但是保留下来之后的虚假,体现的是一个真实。”
▲刘韡:《受难》 展览现场 2014 铁、钢 尺寸可变 摄影:唐萱 图片由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古典情怀与现实主义
2006年,刘韡搬去了自己现在的工作室——位于环铁艺术区附近,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刘韡每天穿梭其中,“这儿生活着社会末梢的人群,也是我们真正的现实,它们混乱嘈杂,聚积着来自于全国各地身份不明的打工者,滋生着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刘韡将这样的社会现实表达为“巴洛克”式的风格,“巴洛克是跟教会、资本、权利有关系的,在这些力量的支配下,奇特、古怪、变形的东西产生了”。
对刘韡来说,灵感来源往往是非常感性的,图像对他的刺激要大于其他。比如他现在还记得小时候看过的一部意大利的片子:《一个警察局长的自白》,其中一个情节令他印象深刻:一个妙龄美女死后,被浇上水泥就直接放在建筑体内以毁尸灭迹。刘韡说:“在我想象中,人们永远都不会发现这具死尸。我还喜欢看动物世界,看迁徙的动物,我会联想到跟人类有关系的工作,周围危机四伏,各种猛兽等待着,这跟建筑很像,建筑发展到一定的时候里面一定藏污纳垢,非常肮脏的各种交易与利益在里边,你会有各种各样的时间联想,各种各样的连通,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是偶然发生的,都有必然的一个系统,每一个链条都衔接着,我最感兴趣的是链条的末梢。这个末梢是被忽略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即便如此,他却从未尝试走进这末梢的人群里,因为他不想用一种关怀的方式去反应这个社会现实,在他看来那是无力的,也是无效的——“我关注的是更深、更宏观、更隐蔽的一个现实,包括自我建构的一个现实,自我建构的现实也是自我的认识与体现。”
刘韡说自己是一位具有古典情怀的艺术家,却用着最观念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他被定义为一位观念艺术家,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建立某种秩序,这种秩序不是为了制造某种规范,而是为了最大化地寻找到自由。他让我们看到一种通过艺术抵达自由的可能:构建一个现实,才能超越现有的现实。
| 文章版权归雅昌艺术网所有,未经授权,严禁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