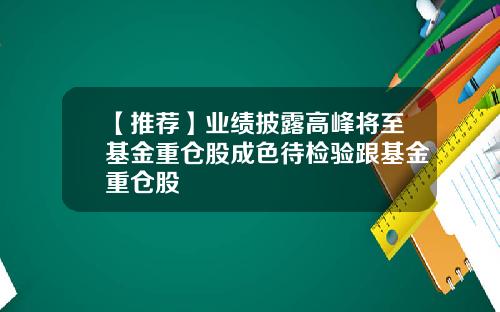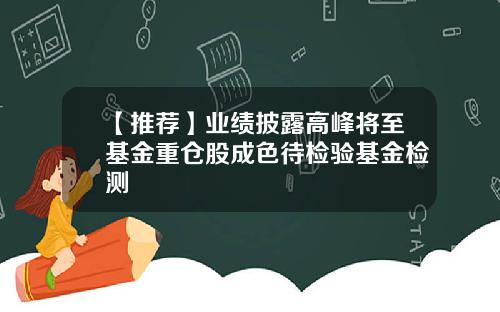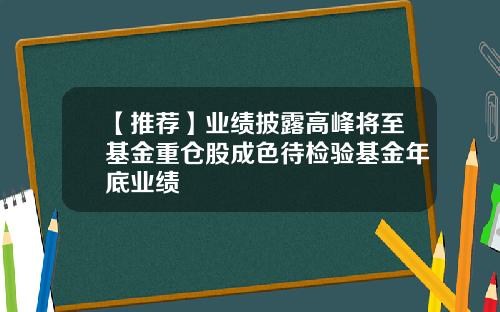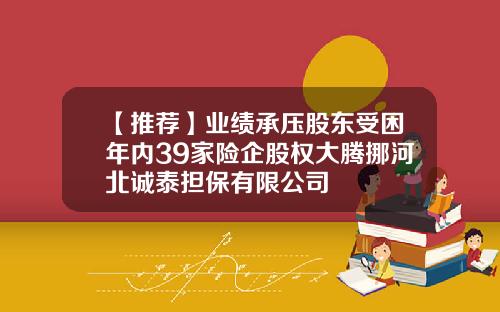山西灵石县段纯村刘氏宗族第五老门生存繁衍历史(编写:刘全旺)
段纯刘氏宗族据考证是从山西洪洞万安村迁徒而来迁徒以前的历史
无法考证,只能从段纯开始记叙。明朝嘉靖年间,刘氏始祖携四子到段纯,
当时此地只是居住着十几户温姓人口的小村庄。外姓人到此,房无一间,
地无一垄,其艰难无比。为寻求更好的生存环境,三子廷祥又迁居到梁家
嫣村,四子(名讳失考)迁居到神堂底村,长子(名讳失考)和次子廷璋
留居段纯,其后代简称一支派和二支派。其中二支派中的四世应先大约于
1625年迁往梁家嫣关原上村,七世曰升大约于乾隆年间迁往两渡村,十
二世永祥大约于嘉庆年间迁往关家庄村,十二世(名讳夫考)大约于光绪
三年迁往介休义棠村。其他还有迁徒外地的有待考证,由于笔者掌握的信
息很少,只能对段纯二支派中五老门其中的第五门的一些情况作简要介
沼。
段纯刘氏二支派发展至六世汉忠时,家业已很雄厚,相传此公在外地
有多处商铺,但不知做何种生意。他生有五子,我辈为第五子日璜之后,
他为五子每人建了一处深宅大院,每宅大院又配备一处小院(大约供仆人
居住),故老家谱中有“汉忠生五子,俗称五老门”的记载。他的一子到
双池村途经官桑园村旁见“一蛇缠绕一兔,认为应了‘蛇盘兔,必定富’”
的传说,必定是块风水宝地,便重金购得此地作坟茔。此地由于面积不大,
只葬有五老门七、八、九三世人,据传当年墓地松柏环绕,碑楼林立,风
铃高挂,风吹风铃叮当响,一派庄严肃穆之势,只可惜离段纯十几里路,
以至后来清明祭扫后代人都因遥远而懒的去。近年来又屡遭盗墓贼盗掘,
一片狼藉。吾辈感叹:墓地豪华,实无必要,不但花了银钱还招来盗掘之
祸,使先人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息,倒不如认真修谱,辈辈相传,免得后
人连祖先名讳都不知,无法寻根,正所谓“树碑不如立传”。
由于家境富裕,六世汉忠以下七、八、九三代人自然均受到了良好的
文化教育,在当时的科举制度下,考取功名不足为奇。1975年因要在段
纯分成沟老坟墓旧址修建段纯粮站,刘氏后人在对其墓穴搬迁进行开棺的
过程中,看到汉忠的孙辈刘健等人均身着官服,说明是有功名之人。取得
剩功名,到异地为官上任,年长日久,在当地通婚成家乃至定居,也是情
理之中,所以五老门中出现断辈现象,可能有些属于这情情形。据上辈人
讲河南归德府(今属商丘市)有刘氏一族,在外为官多年,人称“书部刘
家”,将五老门中的一宅院赠与同族人。笔者在网上查阅“书部”的确是
古代掌管文书档案的朝廷机构,相传一直到清朝末期,“书部刘家”和段
纯五老门的后代还有书信互通和互赠礼品的交往。
近年有山东一家刘氏族人同段纯族人联系,寻根问祖,是否为五老门
之后,有待考证。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因生活所迫而迁徒他乡,如二支派中的义棠一支就
是由12世公(名讳失考)肩挑一担于光绪三年逃荒到介休义棠村的。光
绪三年山西大旱,传说出现了“人食人,狗食狗”的可怕现象,人们四处
逃荒,义棠处在北上太原,西进汾洲府(今汾阳市)的三岔路口,在此找
个糊口营生相对容易一些,听我父亲讲过:1900年(光绪26年)慈禧太
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时在清廷翰林院任职的两渡籍人氏何乃滢拌驾随
行,行至两渡,在何家大院留宿一夜,二日天明赶路登程,众百姓跪地送
行,意欲一睹太后尊容,太后应允,打开轿帘,此时只见太后手持一锭元
宝,百姓不解其意,官员告知,光绪三年,朝廷为每位灾民发放一锭元宝,
但经过层层盘剥到灾民手中仅有两枚铜钱了,清朝官员贪污腐败程度可见
连皇帝都公开承认,而又无可奈何。
五老门第五门从第十代开始,家境开始败落,十世映奎为拔贡,煌奎
为秀才,虽不是官职,但还算有个文凭。到十一代连个文凭也没有了,到
十二代我祖父们这一辈都是简单识些字后便为了生计或经商当学徒或在
村务衣。后来升职最大也就是个商铺掌柜而己,究其因还是经济制约,因
清代没有义务教育,贫寒之家是不可能长时间雇佣私塾先生的。
五老门第五门繁衍到十三代叔伯第兄九人,字辈为“耀”,第三个字
依次为:福、禄、祯、祥、荣、华、富、贵、文,如再生一位,则为耀武。
时值民国时期,虽然家境不富裕,但读书的费用可能相对低一些,弟兄九
人均读过几年的书,当时学校的教材己和清代有所不同,增加了算术等自
然科学内容,我的父亲耀祯还懂得元周率等于3.14;他们读过几年书后,
耀禄、耀祯、耀祥、耀富、耀贵五人均在商铺当了伙计。时逢动乱年代,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以及受日本侵略中国的影响,民族商商业纷纷倒闭,
他们最终又回乡务农。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段纯曾遭到了日本侵略者烧杀,
据灵石县誌记载:日军攻占太原后,分东、中、西三路大举南下,东路经
祁县子洪口进入上党地区直取长治;中路沿汾河流域南下直取临汾;西路
沿黄河边南下。其中中路日军在灵石边境韩信岭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卫立煌
部的顽强阻击,久攻不下,只得调西路日军到韩信岭增援,最终中央军撤
退,韩信岭失守。经过段纯的日军部队可能就是日军的西路增援军。当时
全村人扶老携幼,纷纷避难。我辈当时未出生,只有我姐姐锁玉刚四岁,
随母亲钻入煤窑躲藏,日军途经段纯时开灶造饭,就地取柴,临街商铺门
窗、箱柜被毁焚。日军过后,满目疮夷,一片狼籍,我父亲的中药铺从此
再未开张。因亲身感受日军侵略行径,父辈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程度自
然很深,加之当时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以就有了我叔父耀富加入牺盟
会,耀文加入决死队,耀华更在先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之举。正所谓:
时代造就人,使得草根百姓参与到政治的行列。
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爆发时,我的堂叔耀文在双池读书,双池中
学当时是培育抗日力量的摇篮,它是由双池镇侯家渠村爱国绅士侯德长出
资创办,多名共产党员担任了该校教师,其中有解学恭(70年代曾任天津
市委书记),毛达山(北平大学毕业生,全国解放后曾任西安市人民银行
行长),在这样的氛围里,学生的爱国热忱日益高涨,时值西安事变,国
共二次合作,我叔父刘耀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加了由闫锡山政府和共
产党联合组织成立的“抗日青年决死纵队”(简称决死队),并参加过多次
战斗,终因战争的残酷以及国共合作的破裂而脱离了部队。
五老门第五门繁衍到十四代(即:我们这一代)是“旺”字辈,排行
弟兄十三人,连女儿共19人,除过启旺,金海年纪较大,其余均是新中
国成立后上的学,当时国家困难,高等教育很不普及,所以文化程度都不
高,最高的是我堂姐刘桂兰,也仅是个大专生。十五代是“树”字辈,排
行兄弟姐妹共二十七人,十六代排行兄弟姐妹现为二十二人,这俩代人赶
上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好时代,国力增强,大学扩招,九年义务教育普及,
他们之间不但有大学本科生,还有硕士研究生,均为国家栋梁,相信长江
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盼望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让先辈们曾经
遭受过的饥饿,战争永远不再重演,后代人生活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