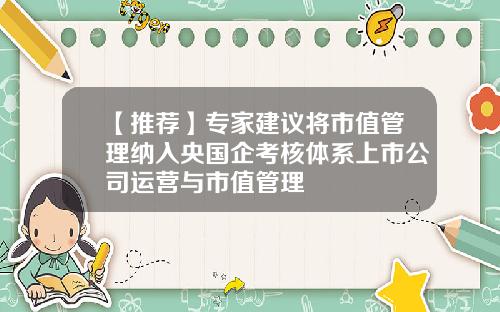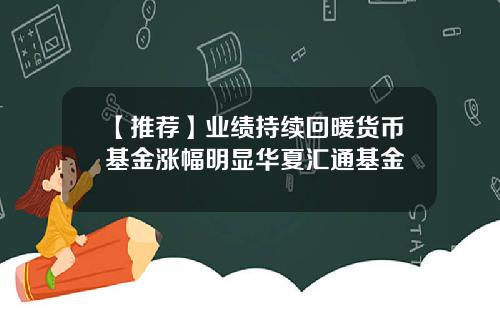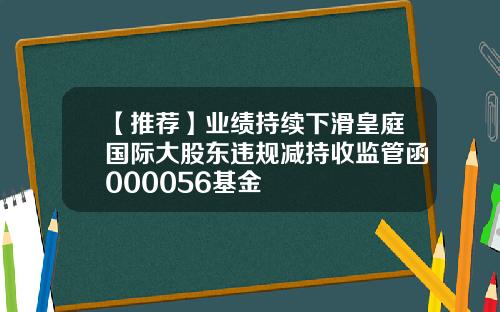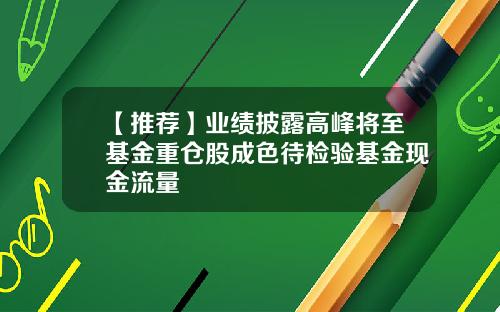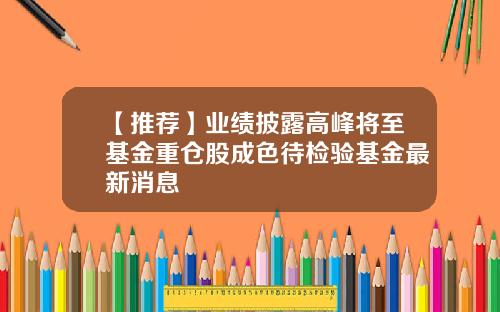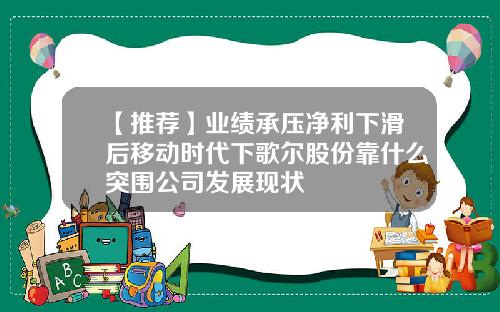江夏门窗维修
文章目录:
1、长江武汉段有座千年古镇,青石板街道遍布老建筑,时光在此静止2、因为这个事,包工头给孩子买车买房的承诺都泡汤了3、不用再“漂泊不定”,不用再两头“摸黑”——四位长江渔民“转身”记
长江武汉段有座千年古镇,青石板街道遍布老建筑,时光在此静止
旅游武汉,所欣赏到的景致必然离不开长江,滨江沿线上,既有自然景点,也有人文景区,每一处都值得细细品鉴。相对于某个独立的景点来说,成系统的人文景区更加令人向往,比如长江武汉江夏段,就有一座千年古镇金口。金口镇虽然面积不大,但知名度颇高,自古以来就是商贾重地,热闹非凡,至今仍保留有一座原生的后山路古街,里面青石板阵阵,斑驳老建筑比比皆是,一砖一瓦宛若被时光尘封,值得一游。
金口镇位于武汉以南,属于远城区江夏地界,实际区位和城区仍有一定距离,已经过了四环线和绕城高速以外,偏远几乎是所有人对它的第一印象。也正是因为距离,让金口的发展有种“自力更生”的孤独感,从千百年前的长江水道,到现在的绕城发展区,古镇的地界始终聚集在金水河畔。鲜有的城镇面貌,纵横阡陌的小路,步梯单元楼,地势反差明显的生活区,在金口古镇毗邻区中走一圈,除了常见的行道树和民房外,似乎很难见到所谓古镇的风貌和气质。
不过,说没有看到古镇风貌,那是因为找错了地方,毕竟即便金口再小,也有大大小小几十条马路和乡道。水域面积丰富,羊肠小路错综复杂,金口古镇变化万千,曾经古老颜值的区域残留在一处叫做花园社区后山路的地方。从名字来看,这是一座社区与道路集合的地方,社区名字很冷门,至于后山路,估计知道的人很多,只是没在地图上标注,仍然局限于当地土著的口口相传中。沿着金岭路向西,过金湖路后就能在一片市井小镇的街景里看到后山路入口,那里就是离金口古镇最近的地方。
花园社区后山路的入口建着一座门牌,并不高调,看着显眼,特别是上面贴着的“金口古镇”标识牌,让人眼前一亮。入口处的地势很低,往里走去逐渐抬高,一条小道向上铺去,两边挤着绵延的老房子,门对门的那种,一看就是很老的布局。小道不是泥泞路,也不是水泥,而是由一块块青石板组成,很有江南民居的风格,天气晴好的时候,走上去,像是踩着斑驳的石墙,清脆得很。来往的人,或推着车或挑着东西,有序避让,刚好容纳通行。
在这样的小路上行走,机动车显然不行,摩托车勉强可以,一阵阵噪音由远及近,响彻四周。青石板的路面从入口一直铺到最里面,路两边的建筑密集之态势也没有任何改善,以至于到里面后,很多建筑之间的楼间距已经近在咫尺。后山路主路是一条南北纵向的格局,并不严密,有些曲折;除此之外,进到里面后还有好几条东西横贯的小路,那是真的小路,宽度在一米左右,上面长满绿草,就是供人步行。也有一些小巷子,露出一截,进去之后发现尽头是民宅,相当于是“死路”。
民房建筑在后山路上是主体,以主路做对称轴分布,还零散种着行道树,非统一规划。这些民房中,有的是新修筑的,两三层砖混结构,铝合金窗户和铁大门,数量不多,但大部分还是颜值非常陈旧的老房子。老房子是焦点,颜值陈旧,风格古朴,斑驳的痕迹和复古的风格与这个年代反差明显。由于是老房子,大门紧锁,看不出是否有居住痕迹,但整体深色系装饰,低矮的楼层和裸露在外的青砖,旁边还钉着门牌,肯定是被登记在册的。
走一圈后山路,看到的老房子和新房子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外观判断依据直观,主要在于外墙,像老房子的外墙多是涂着水泥,风化脱落,颜色有深有浅,且造型古朴。老房子楼层低,绵延建在一起,屋子旁边的树木年龄大,撑开一方树荫,成为绝佳的点缀。人走在树下,感受到清凉的意境,而身后的老房子,蓦然沉睡,没有人居住,鲜有人打理,连偶尔光顾的人也不多,似乎难以唤醒。与外面的热闹比较,后山路上才是真的安静,形成一座真正的古镇意境。
游览金口古镇,会感叹于时光易逝,辉煌热闹终归寂静,那些陈旧的建筑和民房,还保持着老样子,犹如被光阴尘封。寻找古镇需要当地土著指引,小编也是历经曲折后才搞明白,因为直接网络搜索“金口古镇”是找不到的,具体要搜索“花园社区后山路”才能定位准确位置。交通上有公交车可以抵达,乘坐910路或者928路,在“金岭路邮局路”或者“金岭路金口”下即可,同在金岭路上,再根据定位或问路,基本上很快就能到达。
因为这个事,包工头给孩子买车买房的承诺都泡汤了
长江日报融媒体讯(记者魏娜)这个春节,做建材生意的王老板过得很憋闷,因为赌博,他把给女儿买车的20万,和给儿子买房付首付的40万,都输了,还欠了10多万的高利贷。
王老板是黄陂人,在江夏开了一个铝合金门窗建材店,手下有40多名工人,生意十分兴旺,一年的纯利润有四五十万,原本一家人和和美美,但只要他逢年过节回黄陂老家,进屋不到半小时,湾子里的人就上门来。每次回来,他除了睡觉、吃饭,其他的时间几乎都在晃晃室。
去年十一,老王一家在黄陂待了3天,输了近3万,今年元旦小长假,又输了好几万。
由于输赢大,王老板身上也不总是带着那么多钱,每次他把身上的钱输光了,就会有人主动借钱给他,当然借钱是要给利息的,而且利息还不低。去年11月,王老板的老母亲去世了,做了多年建材生意的他,竟拿不出给老人办丧事的钱。
过年前,26岁的女儿找王老板“兑现承诺”,去年初,他承诺给女儿买一辆车代步,可一年过去了,准备给女儿的20万元,都在牌桌上输了;为了让他少输一点,王老板的妻子说要给上大学的儿子买一套房子,王老板答应给首付,可说好的40万首付,也在不知不觉中被他输光了。
大年初一,一家人给过世的老母亲办新年时,要债的人找上了门,家人这才得知,他还欠了十多万的高利贷。
去年一年赚的钱,到了春节分文不剩,还有这么多外债,这让王老板的家人很绝望,“他每次打牌都输,但每次只要有人叫,他就去,完全管不住自己。”为了避开这些牌局,家人一到放假,就想拉他去旅游,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会坐上牌桌。
去年春节,为了躲牌局,他干脆去了上海的哥哥家过年,初七回到黄陂老家,到十五元宵节的8天时间,他输了12万。
王老板的家人想尽办法让他远离牌桌,可他总打着看母亲的旗号回乡赌博,每次看到他经不起牌友几句鼓动就上了牌桌。如今,王老板的老母亲去世了,王家人举家搬走,准备通过阻断他回乡,来杜绝他的豪赌。
【编辑:朱艳琳】
不用再“漂泊不定”,不用再两头“摸黑”——四位长江渔民“转身”记
这是养殖围网拆除前,“渔二代”王贵宝一家在湖北洪湖上的住所(王贵宝提供)。当时王贵宝和家人住在船上,常遭风吹日晒雨淋。下图:2018年,在湖北洪湖市,41岁的王贵宝(右)与父母坐在新家的沙发上(新华社记者熊琦摄)。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1月5日电(记者侯文坤)1月5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四位长江渔民“转身”记:转行转业转产 换赛道换思路换活法》的报道。
心有怀念,脚步向前。随着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实行为期十年的禁捕,长江沿岸世代以渔为业的渔民们向着新生活,“转身”上岸。
(小标题)转 行
32.6公里的长江湖北武汉江夏段水面上,58岁的王明武“漂”了几十年。如今,他已开始新的生活——身着工作服,再次登船,昔日“捕鱼人”成为“护鱼员”。
王明武是江夏区金口街花园社区地地道道的渔民,15岁便在长江上捕鱼。
“捕鱼讲究两头‘摸黑’,过去几十年,几乎每天凌晨4点起床,6点放渔网,中午就在船上做饭吃……”靠着打鱼,王明武后来在岸边有了房,但多数时间还是在船上。
“运气好点,一年下来一家人卖鱼能收入10多万元,但太苦太累。”回忆过去的生活,王明武有不少辛酸与无奈。
由于从小捕鱼,王明武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捕鱼能手,对江里的变化感受深刻。
“小时候和父母一起捕鱼,鱼的个头比现在大多了,产量也更大。水也干净,直接捧江水喝。”王明武回忆说,以前家里一条小木筏,就能养活一大家子人;后来换上了大机船,一年下来却挣不了多少。“近些年,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想捕条大鱼都不容易了。”
金口街是长江初进武汉的地方,打鱼、卖鱼、吃鱼曾是这里每家每户生活的常态。如今,走在金口街的街巷,不少过去以江鱼为特色的餐馆已改换招牌,抹去了“江鱼”字样。
如同王明武告别渔民身份一样,这里“靠水吃水”的人们,都开始了新的营生。
“渔船、网具、船证都被收了,共补偿了11.7万元。我和老伴的医保、社保解决了,每月有几百块退捕生活补贴。”告别了赖以生存的打鱼活计,王明武生活依旧有保障。
不再当渔民,王明武也没离开长江,他与渔政部门签订了劳动合同,成为一名护鱼员。
去年7月1日以来,他每天在岸上徒步巡查,不定时随渔政执法人员一起巡江,一旦接到违规捕捞的举报,即使是在晚上,也会到江上去配合相关部门执法。
“有行船经验,又熟悉长江航道,干这活,我在行。”王明武说,“我们很幸运,还能维系与长江的感情。”
(小标题)转 业
又一年春节临近,湖北洪湖“上岸”渔民王贵宝至今还记得头几年第一次在岸上过年时,一家人高兴、激动,又不自在的情景。
“坐不惯软沙发,觉得蹲在板凳上更舒坦;吃不惯超市里买的鱼,总觉得湖里的鱼更鲜;用不惯方便的天然气,会怀念柴火煮出来的米饭。”王贵宝说,为适应岸上的生活,一家人花了不少时间去磨合。
长江禁渔对于长江生态而言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依靠长江生活的渔民而言,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渔民的甘苦,说不完道不尽。王贵宝黝黑的皮肤,便是最好的见证。
他说,当渔民时,风吹日晒雨淋,挣三四年也抵不上一年亏的。“就是靠天吃饭,2011年遇到大旱灾,家里围网养殖的鱼和螃蟹,绝大部分干死了,损失近20万元。2016年又遭特大暴雨,同样损失巨大。”以前在湖里的生活状态,王贵宝用“摇摇晃晃”来形容。
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下,洪湖生态治理也强力推进,王贵宝一成不变的生活迎来巨变——上岸。
一家人搬进洪湖市区一处现代化居民小区,三室两厅的房子窗明几净,家具家电一应俱全。吊顶白墙取代了渔船的漏风顶棚和桐油木板,铝合金门窗替代了渔船上的透气小窗……
这样一套113平方米新房子,王贵宝用父亲和自己的购房补贴、扶贫搬迁补偿和政府收购渔船的钱凑足了房款,没有欠债。
渔民们较少接受过正规教育,部分还是文盲,许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上岸之后,如何生活?
“真要感谢好政策。”王贵宝说,当地政府为像他一样的渔民对接安置小区,联系工作岗位,通过争取相关政策帮扶。借这次机会,王贵宝开始了新营生——小区附近一家鞋厂的工人,月入3000多元、一天包三顿饭。“今后的生活能不能更有滋味,那就要看自己的本事了。”在工厂几年,王贵宝很珍惜自己的工作,并且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
当初,由于家里穷,王贵宝小学没毕业就上船帮忙养鱼,他希望儿子通过上学改变命运。
“他们‘上岸’比我们早,未来的生活肯定也比我们会更好。”王贵宝深信这一点。
(小标题)转 产
汉江,长江最大支流,承载着无数渔民生计。
在湖北襄阳老河口市王甫洲晨光村,刚满40岁的郑鹏成与哥哥郑鹏展,自出生便住在汉江边。郑鹏展14岁、郑鹏成15岁先后登上船开始捕鱼捞虾。
郑鹏成说,一家人一度发展到四条渔船,而那时汉江梨花湖段,捕鱼的有几百家。渔船往来如梭,开始时用大眼网,后来鱼小了就改用小眼网,到最后发展到满河的地笼子、迷魂阵,甚至用电打鱼,汉江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有时一天能捕20元钱的鱼,都要高兴得不得了。
“汉江的鱼越来越少,我们只好一边捕鱼,一边养鱼,一边收鱼虾加工,增加收入。”郑鹏成说,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越来越深刻感受到,过度捕捞,吃子孙饭、断子孙路,严重破坏了汉江的生态环境,而且这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捕鱼捞虾,也只能勉强地维持最低的生活,应该早些着手在别的行道寻找出路。
2019年,在地方政府支持下,郑鹏成拉上哥哥,以22万元上岸补偿款为本钱,创办了一家小型环保公司,主要承接河道清污除草等业务。
“从靠水吃水,到靠水养水,换条道,换个思路,更有奔头了。”郑鹏成说,随着汉江生态修复工程推进,他手上的业务也越来越多,公司越办越红火。“比如王甫洲水电站清污除草的订单,除了本身的劳务费收入外,我们还将打捞上来的水草,一部分出售给养殖户养鱼养虾养螃蟹用,另一部分就烘干加工成饲料出售,这又能增收好几万元。”
上岸后,兄弟二人变成了河道“清污人”,成为大伙儿眼中转产创业的“先锋”。
如今,郑鹏成的公司用工12人,其中7个都是原来和他们一起捕鱼的渔民。他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接纳上岸渔民就业,一方面希望替政府分忧,一方面这些渔民兄弟水性好、愿做事、靠得住。
“他们月工资平均4500元到5000多元,收入比捕鱼时稳定多了。”郑鹏成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