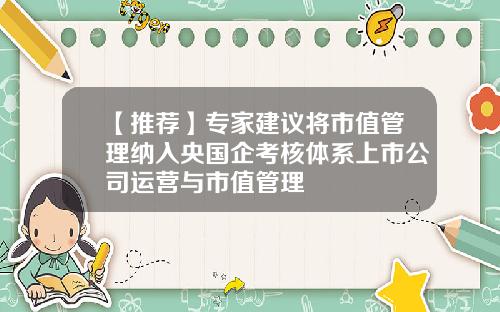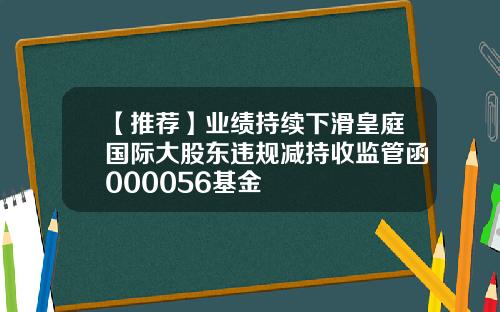并非到处都需要企业家的
并非到处都需要企业家的
并非到处都需要企业家的 MBAChina 张维迎教授在一九八七年写过一篇论文,提出了“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这在当时中国完全计划经济占据各个领域、急需在私有领域能够带领经济发展的企业家群体的时代,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一如中国人物极必反的思维模式,这种和过去完全计划经济相对的理论和思想的冒头,推助了完全市场化的思潮的逐步确立。 二十一年后,《经济观察报》访问张维迎教授,重谈了这个话题,但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不过还是中国经济学界鼓吹了二十多年的完全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的老调子。 按照张教授的逻辑,第一,不需要有国家所有制的领域存在;第二,所有的领域都是需要企业家的。在此潜台词之下,就会非常符合逻辑地得出结论:为了所有领域都能在企业家的带领下发展,因此所有领域都应该被私有化。否则,强调“国家所有制不能产生企业家”又有何意? 国家所有制之下的确不能产生企业家,这个结论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国家所有制领地之内压根儿就不需要企业家,那么,能不能产生企业家又有何关系和影响? “经济”的实质内容就是私有者之间的“交换”,既不是生产,也不是消费,因为生产和消费这些行为自生物存在以来就存在着,而经济二字只有在私有制度之下有交换行为才可以成立。换句话说,“经济”二字与私有制、私有化密不可分。 企业家是经济社会的产物,是私有制的产物而不是国家所有制的产物,是私有者的代表而不是公众的代表,是惟利是图的逐利者而不是天下为公的奉献者。用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个对投资人负责的人。 那么“国”又是什么?如果国家也是以一个私有者的角色存在,那么,这个站在民众对面却又高高在上,操纵着国家机器,掌管着货币发行权,掌控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控制着游戏规则的强者,还能和民众进行公平的交换吗?除了导致强权垄断和强取豪夺之外就再无其它结果了。 因此,国家断不可以国之名义和权力去扮演一个“私”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不能够出于牟利的动机而作为一个市场角色存在。所谓“国不与民争利”就是这个道理。 不能就是不能,国家断不可以一个逐利者的角色进入市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而不是方法问题。既不能直接作为交换者搞“国营”,也不能把公有权委托给企业家去代理市场角色。让企业家作为代理人来参与市场(美其名曰保障国有资产增殖)曲线逐利,同样也是犯了原则性错误。 国家的职能,规范地说就是“服务”二字,服务的对象是全民(公),服务的方式是“社保”。而“服务”和“交换”完全不同,就价值流动来说,服务是单向的价值流动,而交换是双向的价值流动。 经济学人都在谈论市场,也知道市场的符号是价格,张教授就坦诚承认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价格决定论者。可惜的是,经济学人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知道“价格”究竟是什么。价格就是交换的比例,是由作为私有者的交换者之间就两种商品相交换而自愿达成的交换比例。因此,价格既不是两种相互交换的商品之某种商品的自身属性,也不是由超越两个交换者之外的第三方所确定的交易命令。价格是交换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两个交换者对两种商品的价值判断的信号,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价格决定论即西方微观经济学当中的价格自变量理论,它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而且彻底背离了其理性人假定。 说价格是市场信号,这可以说得通,不过价格也仅仅是市场信号而已,而不是市场之外的其它领域的信号,因此,试图将价格机制引入非市场领域的完全市场化思想就是对价格概念的误读。市场就是私有者的交换场,市场上价值流的分布机制是“交换”或者说是价格机制,而在非私有的公有领域,价值流的分布机制是“分配”。交换是价格机制起作用,讲究的是“自愿”,决定权是交换者的私权;而分配讲究“公平”,是法律机制所决定,规范地说决定权是“公权”。因此说,国家所有制领域内不需要企业家。 交换和分配,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流动方式,分配可以看作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价值流动;而交换是横向的、双向的价值流动。交换和分配所适用的所有权制度前提和领域也完全不同。那些标榜深熟此道的经济学家实际上要么对此知之皮毛要么是别有用心地装作糊涂。 那么,国家既不能扮演一个交换者身份,又要以“公”的代表资格为公众提供单向的价值输送服务,它就必然要掌控一定的社会资源。第一,有些资源天然应该属于公众所有,而不应该被代表公权力的法律赋予私人;第二,在关乎民众个体和民族生存的领域,因为支付的代价是“生存”,是无穷大,所以,价格机制不仅无法确立也无法发挥作用。第三,国家要在民生基本需求领域尽到自己的指责,提供服务,也不能没有属于公有的资源。 企业家就是企业家,是一个市场角色,尽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角色,但也仅仅是市场角色,而不是市场外的角色。我们不可能想象政府部门也市场化,让企业家到政府部门去以企业家的思路掌管政府;也不可想象基础教育市场化,让企业家去做校长;不能想象民政慈善组织交给企业家去运作。 在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时向国人提醒国家所有制下不能产生企业家的时候,由企业家主导的西方金融企业纷纷濒于倒闭而被政府接管国有化。雷曼兄弟的老总还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施以援手导致雷曼破产而忿忿不平。而在国内,有些人既要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尚德之士,又不愿再后天下之乐而乐而率先富了起来;有些人既要做优秀的执政党党员,又要做一个对投资人负责而赢利的企业家;还有些经济学人,在国有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当中吃着皇粮,却拼命鼓吹着完全私有化的论调。而更加令人费解的是,这个以“公”为政治路线标志的政府,竟然会容忍这种事情的存在与发展――只有一种解释,执政者已经迷失了(?)自身的角色。